2023年(nián)4月20日(rì),男子吳某某與同事(shì)在羽毛球館打球時,踩到流浪貓肚子上緻摔倒,構成十級傷殘。吳某某遂将羽毛球館所屬公司和流浪貓投喂者肖某某訴至法院。2024年(nián)2月2日(rì),上海市闵行區人(rén)民(mín)法院一審判決,被告肖某某賠償原告吳某某各種費用損失共計(jì)24萬餘元。本案一審裁決後,各方均沒有上訴,因而一審判決于2024年(nián)2月23日(rì)生(shēng)效。但(dàn)判決結果迅速吸引輿論關注,本來(lái)投喂流浪貓是做善事(shì),怎麽變成禍事(shì)?要承擔如(rú)此高額賠償?判決結果明顯超出人(rén)們認知,也引發了理(lǐ)、情與法的沖突。3月27日(rì),澎湃新聞記者從(cóng)上海市闵行區人(rén)民(mín)法院獲悉,依據《中華人(rén)民(mín)共和國(guó)民(mín)事(shì)訴訟法》第二百零九條之規定,經闵行法院院長提交審判委員(yuán)會討(tǎo)論,決定對本案提起再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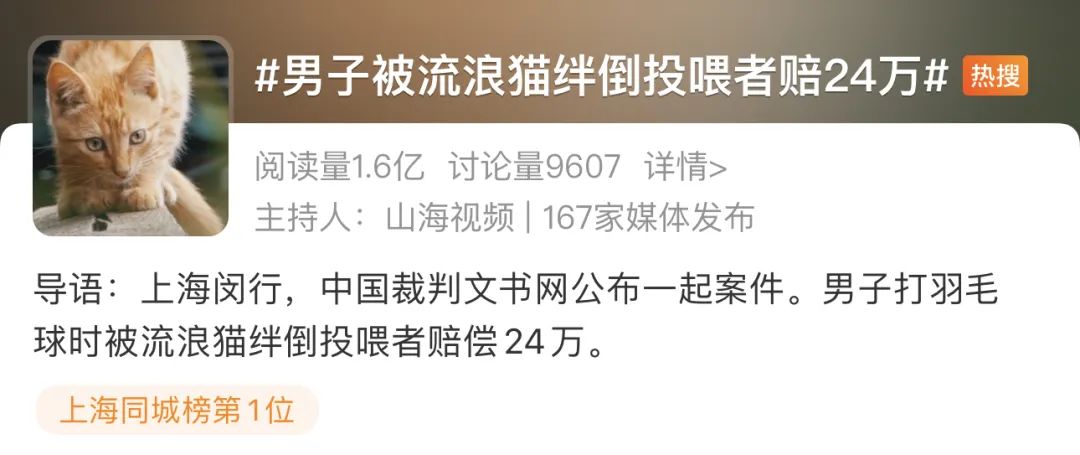
《民(mín)法典》第1245條規定:“飼養的動物造成他(tā)人(rén)損害的,動物飼養人(rén)或者管理(lǐ)人(rén)應當承擔侵權責任;但(dàn)是,能夠證明損害是因被侵權人(rén)故意或者重大(dà)過失造成的,可(kě)以不承擔或者減輕責任。”據此,一審認爲,被告對流浪貓進行投喂,已經成爲動物飼養人(rén),因而判決肖某承擔賠償責任。僅僅從(cóng)文義上看(kàn),所謂飼養是指通過喂養和照(zhào)料來(lái)養育動物,因此,投喂不就(jiù)是飼養嗎(ma)?但(dàn)問(wèn)題在于:在進行法律适用的時候,僅僅看(kàn)法條的文字含義,既不用考慮法條背後的立法目的,也不用考慮各方的利益狀況。法律文字怎麽規定的,我就(jiù)怎麽裁?這是一種典型的機(jī)械司法。

由此聯想到一個古羅馬鴕鳥傷人(rén)的故事(shì)。根據公元前450年(nián)頒布的羅馬第一部法典《十二銅表法》的規定,四腳動物的所有權人(rén)要爲該動物因其獸性而導緻對他(tā)人(rén)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。在迦太基被羅馬打敗後,有人(rén)将第一隻鴕鳥作(zuò)爲戰利品引進羅馬,後來(lái)造成了他(tā)人(rén)的損害。既然法律文字已經規定得(de)如(rú)此清晰,根本就(jiù)沒有解釋空間,如(rú)果機(jī)械地适用法的規定,鴕鳥的所有人(rén)顯然不用賠償。但(dàn)羅馬法學家不這樣認爲,他(tā)們認爲,鴕鳥的所有人(rén)應承擔責任,其推理(lǐ)過程如(rú)下:法律之所以僅規定四條腳的動物的所有人(rén)應負損害賠償責任,而不規定二條腳的鴕鳥緻人(rén)損害賠償責任,是因爲未能預見(jiàn)到還(hái)有二條腳的鴕鳥,四條腳的動物顯然不能解釋爲二條腳的鴕鳥,但(dàn)如(rú)不給受害人(rén)予以救濟,顯然不符合法律的目的和正義的要求。盡管f法律僅僅規定四條腳的動物的所有人(rén)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的規定,其立法目的在于使動物的所有人(rén)盡其管束動物的義務,避免損害他(tā)人(rén),但(dàn)對任何動物,不論其爲二腳或四腳都(dōu)應如(rú)此。因此,基于同一法律理(lǐ)由,關于四條腳動物所有人(rén)的侵權責任,對鴕鳥所有人(rén),應類推适用,鴕鳥所有人(rén)應當承擔賠償責任。
回歸到本案中,僅僅從(cóng)文義上看(kàn),将投喂解釋爲飼養,也是可(kě)以成立的。但(dàn)從(cóng)該條文的立法目的上看(kàn),要求飼養人(rén)承擔法律責任,其前提條件(jiàn)至少有兩個:一是要對該動物能夠進行管理(lǐ)、支配;二是具有一定的利益。說(shuō)到底,在民(mín)法上,動物被視爲動産,是物權的對象。如(rú)果不能進行支配,也不具有利益,就(jiù)不能認爲是動物的所有人(rén)或管理(lǐ)人(rén)。《民(mín)法典》動物飼養人(rén)責任的規定的立法目的在于:促使動物所有人(rén)或管理(lǐ)人(rén)履行管束動物的義務,避免損害他(tā)人(rén)。同時,飼養人(rén)由于享受了動物的利益,因而需要對動物所造成的風(fēng)險承擔賠償責任。有利益才承擔風(fēng)險賠償責任,這才符合公平正義的理(lǐ)念,法本身(shēn)就(jiù)是利益平衡之術(shù)。顯然,本案中,肖某僅僅是投喂實物,既不能支配,也沒有法律上的利益,不管是其本人(rén),還(hái)是他(tā)人(rén),均不會因其投喂食物就(jiù)認爲其變爲動物所有權人(rén)。另外,其在投喂過程中獲得(de)的心理(lǐ)上的滿足或愉悅當然不能視爲法律上的利益。因此,肖某并非“飼養人(rén),其投喂行爲并非飼養行爲。投喂流浪動物本爲善事(shì),善事(shì)不能因法律而變爲禍事(shì)。否則的話(huà),每天有小鳥或松鼠來(lái)到我的窗(chuāng)外,吃(chī)我投放(fàng)的餅幹,我就(jiù)成爲飼養人(rén)了。萬一這隻小鳥撞上飛機(jī),或者這隻松鼠驚吓了老人(rén)、孩童,那就(jiù)真攤上事(shì)了。
總之,在該案中,除了《民(mín)法典》相(xiàng)關規定的文字外,還(hái)需要考量法條的立法目的,考慮當事(shì)人(rén)之間利益平衡的正義理(lǐ)念,對法條中的飼養、飼養人(rén)概念進行準确闡釋,妥當地适用法律。本來(lái),啓動再審并非常規的司法程序,由闵行區法院法院提交審委會主動啓動再審尤爲少見(jiàn),在一審判決後一個多月即啓動再審更是罕見(jiàn),期待再審程序能夠糾正一審中機(jī)械司法的錯誤。本人(rén)在此猜測一下,由于讓流浪貓進入場地,未能善盡場所安全保障義務,再審中,羽毛球館所屬公司可(kě)能成爲主要賠償責任承擔者,而肖某很可(kě)能不承擔任何責任。
回頭再來(lái)說(shuō)一下機(jī)械司法、機(jī)械執法的思維邏輯。所謂機(jī)械司法、機(jī)械執法,就(jiù)是隻知道法條,隻知道法條的文義,隻知道按照(zhào)法條進行“嚴格”适用。既不考慮法條的立法目的,也不考慮對當事(shì)人(rén)之間利益關系的影(yǐng)響,是不是符合正義理(lǐ)念?有沒有造成當事(shì)人(rén)之間利益關系失衡?這種機(jī)械适用規範的情形在生(shēng)活中并不少見(jiàn)。比如(rú),近日(rì),一則“斷臂男子在武漢欲免費乘坐(zuò)地鐵被工(gōng)作(zuò)人(rén)員(yuán)要求出示殘疾證”的新聞沖上熱(rè)搜。眼裡(lǐ)隻認殘疾證,沒有殘疾證,即使肉眼可(kě)見(jiàn)的缺胳膊少腿,都(dōu)不認爲是殘疾。從(cóng)形式上看(kàn),地鐵工(gōng)作(zuò)人(rén)員(yuán)是在嚴格執行相(xiàng)關規定,必須見(jiàn)到殘疾證才能夠免費乘坐(zuò)地鐵,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機(jī)械執法。眼裡(lǐ)隻有法條,看(kàn)不到相(xiàng)關規定的目的是給殘疾人(rén)士提供方便和優惠,不是增加負擔。在是否殘疾問(wèn)題上,不相(xiàng)信自(zì)己的常識判斷,不懂(dǒng)得(de)社會經驗法則(缺胳膊少腿當然屬于殘疾範疇)。機(jī)械适用法條的人(rén)是法律的門(mén)外漢,他(tā)們似乎純粹活在一個法條的世界中,既不考慮法條背後的理(lǐ),也不考慮法條背後的情,必然造成法、理(lǐ)、情三者的脫節,導緻執法和司法結果脫離(lí)常識,違背人(rén)情。
怎麽克服機(jī)械執法、機(jī)械司法?關鍵之處在于:充分(fēn)認知法并非就(jiù)是個别法條,除了具體(tǐ)規範以外,還(hái)包括立法目的、正義理(lǐ)念以及各種法律原則。法條固然具有直接的規範性,可(kě)以直接适用。但(dàn)法條是極爲有限的,無法應對無限複雜的世界;法條是滞後的,往往難以跟上快(kuài)速變化的世界。因此,執法、司法過程中必然涉及到法條的解釋,除了法條以外,還(hái)需要充分(fēn)考量立法目的、正義理(lǐ)念以及各種法律原則。在這些要素的指引下準确适用法律,對法條進行解釋,有時候需要擴張解釋,有時候需要限縮解釋。在法條存在漏洞、不敷使用情況下,還(hái)需要進行類推适用、目的性擴張或限縮等方式續造法律。當然,刑法中禁止類推适用。法律适用的本質是在法的安定性(主要體(tǐ)現爲嚴格司法)、正義理(lǐ)念(人(rén)與人(rén)之間利益關系平衡)以及立法目的等三者之間進行綜合平衡,猶如(rú)在三個雞蛋上跳(tiào)舞,既要考慮法條的具體(tǐ)規定,也要考慮正義理(lǐ)念(利益關系平衡)、立法目的,這是三個維度上的思考,是一個創造性智力勞動的過程。在事(shì)實認定過程中懂(dǒng)得(de)應用社會經驗法則,在法律适用中懂(dǒng)得(de)價值衡量與判斷,執法者和司法者不僅需要智慧,需要具備法律素養,更需要有擔當的勇氣。




 請(qǐng)掃描關注豐國(guó)官微
請(qǐng)掃描關注豐國(guó)官微